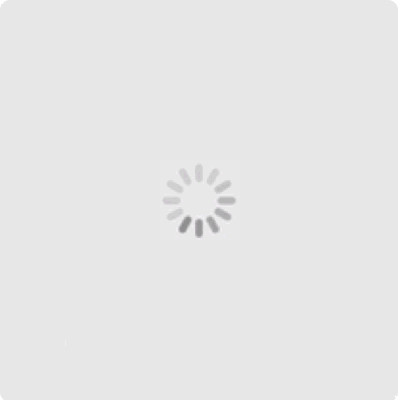一、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其他長輩小時候分別玩過的游戲。
長輩小時候玩過的游戲有跳皮筋、踩氣球、跳房子、玩彈珠、打四角包。
1、跳皮筋
跳皮筋,也叫跳橡皮筋、跳橡皮繩、跳猴皮筋,是一種適宜于兒童的民間游戲,約流行在20世紀50至90年代。
皮筋是用橡膠制成的有彈性的細繩,長3米左右,皮筋被牽直固定之后,即可來回踏跳。可三人至五人一起玩,亦可分兩組比賽,邊跳邊唱非常有趣。先由倆人各拿一端把皮筋抻長,其他人輪流跳,按規定動作,完成者為勝,中途跳錯或沒鉤好皮筋時,就換另一人跳。
2、抓石子
扔五個石頭在地上,然后拋一串珠子抓石頭,最后接住珠子......這個游戲小時候很受歡迎,難度也挺大,手小的人很難抓。而且不僅是抓石子,還可以抓麻將,豎著的麻將代表一千,橫著的是一百,平攤著的是十,一般誰先抓到一萬誰就贏了。
3、跳房子
這個游戲的玩法很簡單,扔一個瓦片狀的石頭在空格里,然后單腳跨過有石頭的空格,經過每一個沒有石頭的空格,回來的時候再單腳撿回石頭,繼續扔在下一個空格上,誰先扔到最后一個空格誰就贏了。
4、玩彈珠
用一個大彈珠在土里鉆個洞,這個洞叫老巢,然后把小彈珠彈進洞里。誰先彈進去,就能用大拇指和食指量一拃,再去攻擊其他人的彈珠。如果打中其他人的彈珠,并且打中后兩個彈珠相距小于三拃,那個彈珠就屬于你了。
5、打四角包
記得小時候很多多余的書從來不會扔,用來折四角包最好不過了,尤其是書殼做的最硬了。那時候幾乎每個男孩子手上都有一摞四腳包,隨時準備下課“應戰”。
玩法也很簡單,每人放一個四角包在地上,誰力氣大用自己的四角包把別人的四角包打翻了,別人的就屬于你了。
二、長輩小時候玩過的游戲有哪些
長輩小時候玩過的游戲有跳皮筋、踩氣球、跳房子、玩彈珠、打四角包。
1、跳皮筋
跳皮筋,也叫跳橡皮筋、跳橡皮繩、跳猴皮筋,是一種適宜于兒童的民間游戲,約流行在20世紀50至90年代。
皮筋是用橡膠制成的有彈性的細繩,長3米左右,皮筋被牽直固定之后,即可來回踏跳。可三人至五人一起玩,亦可分兩組比賽,邊跳邊唱非常有趣。先由倆人各拿一端把皮筋抻長,其他人輪流跳,按規定動作,完成者為勝,中途跳錯或沒鉤好皮筋時,就換另一人跳。
2、抓石子
扔五個石頭在地上,然后拋一串珠子抓石頭,最后接住珠子......這個游戲小時候很受歡迎,難度也挺大,手小的人很難抓。而且不僅是抓石子,還可以抓麻將,豎著的麻將代表一千,橫著的是一百,平攤著的是十,一般誰先抓到一萬誰就贏了。
3、跳房子
這個游戲的玩法很簡單,扔一個瓦片狀的石頭在空格里,然后單腳跨過有石頭的空格,經過每一個沒有石頭的空格,回來的時候再單腳撿回石頭,繼續扔在下一個空格上,誰先扔到最后一個空格誰就贏了。
4、玩彈珠
用一個大彈珠在土里鉆個洞,這個洞叫老巢,然后把小彈珠彈進洞里。誰先彈進去,就能用大拇指和食指量一拃,再去攻擊其他人的彈珠。如果打中其他人的彈珠,并且打中后兩個彈珠相距小于三拃,那個彈珠就屬于你了。
5、打四角包
記得小時候很多多余的書從來不會扔,用來折四角包最好不過了,尤其是書殼做的最硬了。那時候幾乎每個男孩子手上都有一摞四腳包,隨時準備下課“應戰”。
玩法也很簡單,每人放一個四角包在地上,誰力氣大用自己的四角包把別人的四角包打翻了,別人的就屬于你了。
三、「散文」 憶當年,我們玩過的那些游戲
作者:唐風漢韻//責編:一默
同事們聊天,話題扯到了孩子們的游戲,大家感慨萬千:“現在的孩子幾乎沒有出門的,全都被電子游戲宅在了家里。”
感慨之余,不由鉤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當年和小伙伴們一起瘋的歲月……
無法追尋,卻也無法忘記。
一、打木耳
這個“木耳”可不是吃的那種東西,而是我們童年玩的最多的一種玩具。
“耳”也許是我們當地的方言,我花了很多心思尋找它的學名,可惜沒有找到,查閱字典也沒找到更合適的字來稱呼,所以只能用這個字來代替。
木耳有兩種,一種是用來打擊的,把一個巴掌長的木棒削成兩頭尖尖的樣子,這就是“耳”。把耳平放在地上,用木棒去敲打,待它彈起時,木棒迅速用力擊打,如果擊空了,就失去了連續擊打的權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對方擊打,哪方先到達指定的地點就是勝利。
每當放了學,街上總跑著一大群男孩子,跑著,叫著,跳著,爭著,他們時而為己方的勝利而歡呼,時而因對方的失誤而喝采,青天如玉,冬陽似金,彎彎曲曲的土街,被他們攪擾得快樂起來,天本來很冷,大人們都穿著厚厚的粗布棉襖,而這些奔跑的孩子卻都敞開了懷,袒露出他們的肌體,他們的臉上掛著汗珠,整個街筒子里都擠滿了他們的尖叫聲。
那些院子里閑坐著抽著旱煙的男人,或者大門口盤著腿納鞋底子的女人,嘴里常常點評著:“你聽,這個李三的聲音真尖,直直地鉆了耳朵眼子里,嗡嗡地響。”大家談著,笑著,可都沒誤了自己手中的活計。
另一種耳是用來抽(用我們當地的土話是rou,沒對應的字,只能用這字代替)的,這種耳倒是有通俗的名字,有的地方叫”陀螺”,有的地方叫“打不死”,有的地方叫“打不改”而我們當地就叫“抽(rou)耳”。這種耳做起來非常費事,而且很是個技術活,如果哪家的孩子有一個漂亮的抽耳,很能吸引眾人羨慕的目光。
這就是我童年常玩的抽耳
做耳的時候,先是找一根粗細合適的筆直的木棒,一端鋸得平平的,另一端用刀慢慢地削尖,削得要圓,尖要正,如果尖不正,這個耳難看不說,往往轉不起來,削好尖之后,還要小心地在尖上挖一個小洞,然后塞進一粒鋼珠兒,好看自不必說,珠子轉起來更靈敏,更有一些細心人家,還在平的那端套上一個輪軸的外環,或者用油彩或者臘筆把整個耳涂得色彩繽紛。
做好了耳,大家就互相叫喊著,去村中的西坑(村中有三處池塘,當地習慣稱為坑)的冰上去比賽,看誰的抽耳轉得久,看誰的抽耳轉起來更好看,在比賽的間隙,常常有壞小子從遠處的冰上滑過來,撞到了圍觀的孩子,被撞倒的孩子四蹄朝天地從冰上滑出好遠才停住,大家都快樂地叫了起來,因為冰早被孩子們弄得很光滑,孩子們又都穿著笨重的棉襖棉褲老棉鞋,所以爬起來的時候很費力,被撞倒的一邊爬起來,一邊嘴里大聲地罵著,圍觀的孩子們則在旁邊笑著,跳著……
因此而發生的打架當然也是有的,但更多的時候是笑,是鬧,撞倒了也就爬起來,挨罵的也就沒聽見似的,沒誰太當回事兒,就是真的打起架來,只要不嚴重,哭幾聲,掉幾粒子眼淚也就完了,沒聽說哪家大人幫腔助陣兒。
二、砸坷垃仗
七零后或者年齡更大一點的朋友可能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年齡小一點的朋友就很難想象怎么會玩如此野蠻的游戲,那就通過文字腦補一下大概的場面吧。
村子如果不是很小,那男孩子們自然會分成不同的群體,不同的群體之間各有自己的領地,如果你侵犯了對方的領地就一定暴發戰爭,于是雙方約定,某天某時某個區域開始戰斗。
這可不是小事兒,現在回想都有點后怕,可當時只覺得熱血沸騰,雙方的“司令”就會布置各自人馬,準備武器彈藥,所謂武器彈藥就是坷垃蛋子或者石頭塊子,人們都進入了各自的陣地,然后就有一方沖過來了,喊著跑著,手里往對方扔著坷垃或石頭,屋頂上,墻頭上,柴禾垛后面,街頭拐彎處時時會有坷垃石頭飛過來,我那時還小,親眼看到一個孩子被飛來的石頭砸破了頭,哭著離開了戰斗,我也發現了保護自己的竅門,躲在兩堵墻圍成的墻角內側是最安全的,不論哪方過來的石頭都不會砸到自己——唉,那時我就想,是自己聰明呢,還是自己膽小鬼貪生怕死?
這種游戲因為太危險,更因為常常有孩子鮮血直流以至于家長鬧起了糾爭,漸漸停止下來,但那刺激的場面卻一直浮現在我腦海里。
那個時候,我們最崇拜的莫過于解放軍或者志愿軍戰士,王成、黃繼光、邱少云是我們模仿的對象,作為崇拜的實證,我們也像電影中的戰士們一樣戴一頂柳葉或者楊葉編成的帽子,說是帽子其實就是編成一個環套在頭上,很像奧運會冠軍頭上的那頂桂冠。
那時我們的書包很輕,那時我們的作業很少,那時我們小學只學語文、數學和自然,即使老師布置作業,也大多放學之前就已完成,所以放學后,我們扔下書包就往外跑,折柳枝或楊樹枝,彎成環,然后精心編好,要讓樹葉兒抖擻著精神,要讓樹葉兒在我們跑起來時刷刷作響,那時,我們就覺得自己也成了勇敢的解放軍戰士,我們也儼然變成了英雄,如果誰要是腰里扎上條寬寬的武裝帶,那牛逼勁兒簡直就像祖宗八代都中過狀元!
三、看電影
那個時候,如果村里來了電影,或者聽說鄰村要演電影,那我們高興得簡直就像過大年。
本村演電影自不必說了,放了學就往大隊部跑,搬石頭占窩兒,劃出各種各樣的符號圈地兒,少不了因為爭地方爭吵打架兒,不到電影開演的那一刻,這些糾紛沒有停止的時候,當電影開演了,看到外村的氣喘吁吁地跑過來了,心里就生出一份自豪來。
到鄰村去看電影,對于我們那個時代的孩子來說,誰沒過這樣的經歷呢,別說我們男孩子,就是女孩子也是經常的事啊!那時的孩子可真叫個皮實,三里五里不叫路,八里十里不在乎,撒開腳丫子跑就是了——別說沒自行車,就是有,誰家也舍不得把唯一的自行車放手給孩子們敗壞啊——只要一聽說哪村要演電影了,我們就會像狗皮膏藥一樣粘在那些大孩子后面——沒辦法,他們總嫌我們小,跑得慢,礙事,不愿意帶我們去。
其實,要是我們也知道路,誰稀罕看他們的臭臉子,誰樂意當他們的尾巴啊——放了學,趕緊把書包放下,看看鍋里有沒有能吃的東西,隨手抓起兩塊干糧(那時還吃不上饅頭,大多是死面餅子或者窩頭,有時是煎餅),胡亂夾幾片咸菜就往外跑,一看那些大孩子還在,我們就長舒了一口氣,藏在一個墻角里,等他們要走了,我們就偷偷地跟在后面,那些大孩子們可真壞,他們要么是黑著臉子呵斥,要么是舉著拳頭嚇唬,有時是撒開丫子快跑,太小瞧我們了,為了看電影,我們早就練成了厚臉皮、傻大膽還有兔子它爺爺的速度!到大的小的都累得氣喘吁吁像一群攆乏了的豬,一看實在甩不掉我們,他們就在路邊歇息——他們也真不忍心把我們扔在半路上啊,嘿嘿,歸根到底,大上幾歲就是哥(這只是按年齡,要按輩分,他們中可能有侄子孫子當然也可能有叔叔爺爺呢),良心還不是大大的壞啊。
就這樣蹦著跳著,唱著笑著,打著鬧著,喘氣間就聽到了演電影的喇叭聲,就遠遠地看到了提著馬扎搬著凳子的人群。嘻,又看上電影了,心里那個美勁,豈一個“得”字說的!
散場后,我們又和來時一樣說說笑笑地往回走,小村里,各家的燈光漸漸亮起來了,那一點點昏黃的燈光好像家里人等待的眼睛,夜色似乎淡了許多,彌漫著一股柔柔的暖暖的東西。靜靜的路上,空氣里蕩漾著歡樂的氣息,微風輕吹,爽爽的;多情的月兒在頭頂靜靜地照著,我們走,它也走,好像一直在陪伴著我們,調皮的星星還未入睡,不時地眨著眼睛,好像在取笑著我們,蒼黑的起伏的群山把天圍了一圈,絕似月兒和星星搖籃的花邊,——從沒想到,黑夜的原野竟然是這個模樣——沒有吃人的妖魔,沒有吸血的鬼怪,墳頭倒是有的,黑黑地,靜默在路旁的莊稼地里,但沒有飛竄的舞動的鬼火!
我們歡笑著,打鬧著,路邊樹上的鳥兒被我們吵醒,它們尖叫著,從樹上竄起,撲啦著翅膀在空中盤旋;玉米長高了,吐線了,黃豆結莢了,鼓圓了肚皮,在這清涼的靜謐的深夜,混著種種草的味兒,散發出一種有點甜有點腥又有點香的氣息,更加誘人的是那成熟的瓜兒,隨風飄來香味讓我們饞涎欲滴,肚里的饞蟲抓撓著我們的胃拱著我們的心,就會有大孩子慫恿我們去偷瓜,嘴饞是一定的,但當真有幾個家伙蠢蠢欲動時,就會招來一陣笑聲,當然還有瓜地里照來的手電筒的警示……
回到家時,差不多半夜。有的人家留著門,大多數早已入睡,出來開門的如果是當娘的還好,最多罵幾句就算結束,要是當爹的出來,那很可能是進了大門就被睡眼惺忪的老爹踢上幾腳或在屁股上蓋上幾個手印。那時的孩子可真皮,挨了揍哪有幾個哭的啊,大不了咧咧嘴就把淚水咽了肚里——可不哭,怪丟人的,傳出去以后誰還樂意和你玩啊,男孩子挨幾下揍屬于家常便飯,就當是營養不足加個餐吧。
四、打麥場上練武術
那時大概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打麥場,麥子打完了,場也不耕起來,只在里面堆放麥秸垛兒,一座一座地間隔不遠,圍在場邊,在月光下就像蒙古包兒似的,而我們這些甚至上了初中的孩子,每晚幾乎都會聚在打麥場里,回想起來,那時電影或者電視上武打動作片正盛,從《神秘的大佛》《少林寺》到電視劇《霍元甲》《陳真》,整個社會掀起了習武的熱潮,而我們這些男孩子,更是做夢都想著當大俠,夢想著練成一門絕招橫行天下,于是,我們就常常聚在打麥場上,模仿著電視上的招式,如果哪個伙伴有一本少林武術圖譜,那就成了我們的寶貝,我們對著圖譜研究,然后在月光下嘴里大聲吆喝著,一招一式的練著,雖然最終我們沒有一個人成為大俠,即使有個伙伴跑到了河南也沒能最終成為和尚更沒能成為武術大師,但當年我們月光下打麥場習武的場景卻成了我心頭不滅的回憶……
回想我的童少時代,日子是貧苦的,但對我們孩子來說卻也是自由的,家長基本沒人過問我們瘋玩,甚至連作業都很少打聽,我們放學后,扔下書包,拿一個窩頭,塞一塊老咸菜,或者扯一張煎餅,卷一棵蔥,邊吃著邊往外跑,生怕去晚了就沒人給玩似的。
男孩子們在一起,摔跤是經常的游戲
也許大人覺得孩子就應該玩吧,不出去玩,在家里憋著還得點燈熬油,那不是敗家子嗎?別說小孩子,就連大人,如果天還沒有黑透,沒有哪家人點燈做活的,那個時候家家都是煤油燈,看到哪家的燈亮了,就會有人嘲笑不會過日子,“白天沿街喝茶,晚上點燈剝麻”。孩子出去后,大人們也搬個凳子,或者在大門前的石頭上坐著,男人們銜著煙卷,女人們手里拿著好像納不完的鞋底子,一邊干著自己的活,一邊扯東道西。
大人們對我們最不滿意兩點,一是鞋壞得太快,一雙鞋大人們可以穿三個月甚至半年,可到我們腳上,幾乎一個月就爛得不成樣子,所以當娘的永遠在納鞋底子,她們罵我們“吃鞋”;二是我們的肚子似乎永遠管不飽,轉個圈就餓,似乎肚子里有哪個壞神仙給了“化食丹”,于是當娘的在一起,常常叨叨的就是“喂不飽的豬”“上輩子饞死鬼托生的貓”。
那些年天空真得很藍,藍得簡直像童話,像初生的孩子那純潔的雙眼;
那些年河水實在太清,清得讓人想入非非,像小學同桌女孩那甜甜的笑容;
那些年書包很小,里面裝著可憐的三五本書;
那些年作業很少,經常只有一兩道習題;
那些年日子很苦,最大的愿望是掀開鍋蓋能抓到窩頭;
那些年,我們確實也很快樂……
走遠了,不再回來,找不到任何痕跡。
只能用筆,探入時間的深坑,打撈點滴絕版的回憶。